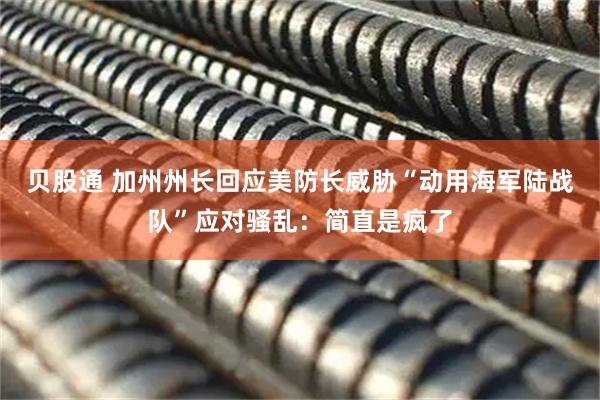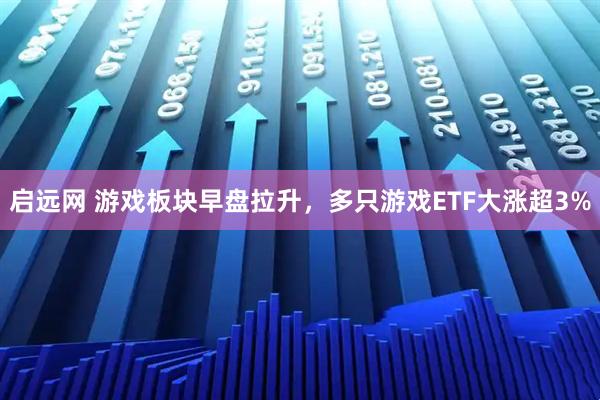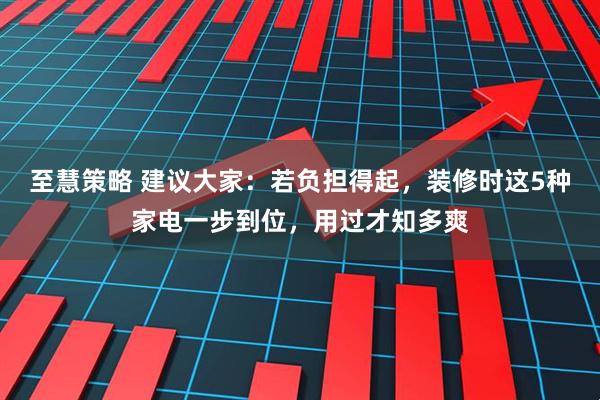“人饿到极致,心是冷的,连血都是干的。”1978年冬,小妹饿得只能抓墙皮充饥。我踏着没膝的深雪去姑父家求粮,本以为是跪来的半袋救命米,谁知母亲却在米袋底摸出一颗带血的金牙和一张退婚书。那一刻我才明白,这哪里是粮,这分明是姑姑生生拔掉牙、签下休书换来的遣散费……
【1】
1978年的冬天,雪下得邪性。
那雪片子比鹅毛还大,落在脖颈子里,像是要把人最后一点热乎气儿都给勾走。
我蹲在破土屋的门槛上,胃里像是塞了一把生了锈的钢丝球,每喘一口气都剌得疼。
展开剩余87%屋里,五岁的小妹正趴在泥地上,指甲缝里全是黑泥。她在抓墙皮吃。
“小五……苦……墙皮苦……”
小妹哭得没声儿,只有两行浑浊的眼泪在黑乎乎的脸上冲出两道白印子。母亲瘫坐在炕沿,手里攥着一个空得能照见人影的米袋子,眼神散得聚不拢光。她已经三天没下炕了。
“妈,我再去一趟。”
我站起来,把腰上的草绳勒紧了两个扣,试图把那个空落落的胃勒得死一点。母亲没说话,只是从怀里掏出一个洗得发白的手绢,颤舞着打开,里面是两毛钱。
“去……去你姑家吧。你姑父虽然心狠,但总归是你亲姑。”
我接过那两毛钱,一头扎进了足以没过膝盖的深雪里。
【2】
从我家到邻县的姑姑家,整整十五里地。
我穿着一双露了脚趾头的草鞋,每走一步,脚趾缝里就钻进一撮雪,冻成冰渣子,再被脚心的热气化成血水。我没敢停,我怕一停下,我就成了这荒郊野外的一座冰雕。
姑姑家是那一带少见的青砖房,门口挂着两盏红灯笼,在白茫茫的雪夜里红得像两只贪婪的眼。
我姑父王德财是公社的红人,家里掌着种子的分配权。可他这人,心比石头还硬。我站在朱红色的大门前,手举起来又放下,反复了几次,才敢敲响那冰冷的门环。
“谁啊?大半夜的,寻死呢!”
屋里传来姑父不耐烦的吼声。门开了一道缝,一股浓郁的肉香味顺着缝隙钻了出来,勾得我胃里那把钢丝球猛地转了一圈。
姑父披着油光锃亮的皮袄,见是我,一张老脸瞬间垮了下来:
“小五?你来干啥?又是来打秋风的?”
“姑父……求您借点粮,小妹快饿死了……”
我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,还没来得及磕头,就被他一脚踹在肩膀上。
“滚!你们林家就是一群吸血鬼!再敢上门,我打断你的腿!”
门,“砰”地一声关上了,差点夹掉我的鼻子。
【3】
我就那样跪在雪里,看着那两盏红灯笼。
过了约莫一刻钟,门又吱呀一声开了。姑姑林素琴悄悄探出头来,一把抓住我的胳膊,把我拽进了耳房。
“小五,快,快进屋暖和暖和。”
姑姑压低声音,语气里全是惊恐。借着昏暗的煤油灯,我才发现姑姑有些不对劲。她总是用右手捂着右边腮帮子,说话的时候嘴角歪着,声音沙哑且漏风。
“姑,你咋了?”
“没事……牙疼,老毛病了。”
姑姑眼神闪烁,不敢看我。她把我带到灶台边,偷偷盛了一碗稀得见底的米粥。我刚喝了一口,正屋里就传来姑父的咆哮:
“林素琴!你死哪去了?老子那半袋种子粮呢?你敢动一粒,老子揭了你的皮!”
姑姑浑身一抖,碗里的粥差点洒在身上。她惊恐地看了一眼正屋,又看看我,眼神里闪过一抹我看不懂的绝望。
那一晚,我被关在冷得像冰窖的柴房里。迷迷糊糊中,我听到隔壁传来重物撞击声,还有姑姑压抑的哀求。
【4】
后半夜,风停了,月亮惨白惨白地挂在树梢上。
我正蜷缩在干草堆里发抖,柴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。一股浓重的药味和血腥气扑面而来。姑姑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布袋,跌跌撞撞地挪到我面前。
“小五……快,起来,趁他喝多了……”
她一边说着,一边把那个布袋死命往我怀里塞。我手猛地往下一沉,那是粮食!实打实的白米!
“姑,这……这不能拿,姑父会打死你的!”
我惊恐地推辞。姑姑却突然死死抓牢我的手,她的手冰凉刺骨,指缝里似乎还带着黏腻的液体。
“拿着!快跑!原路返回,千万别回头!”
月光下,我看到姑姑的半边脸肿得厉害,嘴角还有没擦干的红痕。她说话时的声音更漏风了,断断续续的:
“告诉你妈……省着点吃。姑……以后不能去看她了。”
我背起那袋米,那是全家人的命。我跑出大门的时候,回头看了一眼。姑姑站在雪地里,单薄得像一张随时会被撕碎的纸。
【5】.
我到家的时候,天刚蒙蒙亮。
母亲没睡,她一直坐在门口。看到我背着粮袋回来,她眼里爆出一道惊人的亮光。
“借到了?真的借到了?”
母亲颤抖着手解开袋子,当她看到里面竟然是晶莹剔透的白米时,整个人都呆住了。
“这……这不对,你姑父咋舍得给白米?”
母亲嘀咕着,手在米里胡乱翻找。突然,她的指尖触到了一件硬邦邦、冰凉凉的东西。她猛地往上一提,一个用旧手帕层层包裹着的红布包被拽了出来。
布包上布满了暗红色的污渍,有些地方已经干结。母亲的手开始剧烈颤抖,她一点点揭开那层布。
那一刻,屋子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。母亲的喉咙里发出一声呜咽,随后整个人软绵绵地瘫了下去。
“妈!你怎么了?”
我急忙抢过那个布包。只见手帕里躺着两样东西:一颗还带着一丝血丝、泛着冷黄色光泽的金牙。还有一张揉得皱巴巴的字据,上面按着一个惊心动魄的血手印。
我虽然不识字,但那三个大字我认识:“退婚书”。
这哪里是借来的粮,这是姑姑用命换来的“遣散费”啊!
【6】
真相远比饥饿更让我窒息。
姑父王德财早就不想和姑姑过日子了。那天夜里,他把那半袋准备换钱的种子粮拎出来,摔在姑姑面前,冷笑着让她在“娘家命”和“婆家地位”里选。
他盯上了姑姑嘴里那颗唯一的陪嫁金牙,那是奶奶当年熔了金戒指给她镶上的。
“想要粮,就把这金牙拔了。你身上一根毛都是我的。”
姑父随手扔了一把生了锈的老虎钳。姑姑看着那半袋米,想到了家里饿得抓墙皮的小妹,她捡起了钳子。
在那间冰冷的耳房里,她忍着剧痛,生生把那颗连着肉的金牙从牙床上拔了下来。鲜血喷了一地,她却连叫都没敢叫出一声。
她签下了那份净身出户的字据,把这辈子最后的尊严,都装进了这半袋米里。
母亲趴在米袋子上,哭得嗓子都哑了。那一天,我们全家人围着那锅浓稠的米汤,谁也咽不下去。小妹喝了半碗,天真地问:“哥,这米咋是甜的?”
我看着那颗金牙,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碗里。
【7】
几天后,雪化了。父亲带着我发了疯一样去邻县找姑姑。
王德财家正张灯结彩,新媳妇刚进门。他站在高阶上,满脸横肉都在抖,说林素琴死哪儿去跟他没关系。
我们在后山的乱石窖里找到了姑姑。她蜷缩在一个废弃的守林屋里,身上只穿着那件单薄的破棉袄。她发着高烧,神志不清,嘴里还在念叨:“小五……跑快点……”
父亲背起姑姑往回走,我跟在后面,手里死死攥着那颗金牙。
那一年的春天,日子一天天好了。可姑姑的身体却再也没能养回来。她的半边脸一直有些歪,说话也总是含混不清。
她就在我们家长住了下来。无论日子过得多么富裕,她从来不吃白米饭。她说,那白米饭太贵,她舍不得。
多年后,我事业有成。姑姑走的那天,八十六岁。我坐在她床头,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布包,里面是一颗我托人专门定制的纯金义齿。
我把金牙轻轻塞进她那只满是老茧的手心里。姑姑笑了,那是她几十年来笑得最舒展的一次。
她闭上眼的时候,窗外又开始下雪了。我推开门,看着漫天飞舞的洁白。这一次,雪花落在脸上,竟是暖的。
发布于:湖北省浙江配资网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富鑫中证 销量翻倍、订单排满 节前消费市场活力十足
- 下一篇:没有了